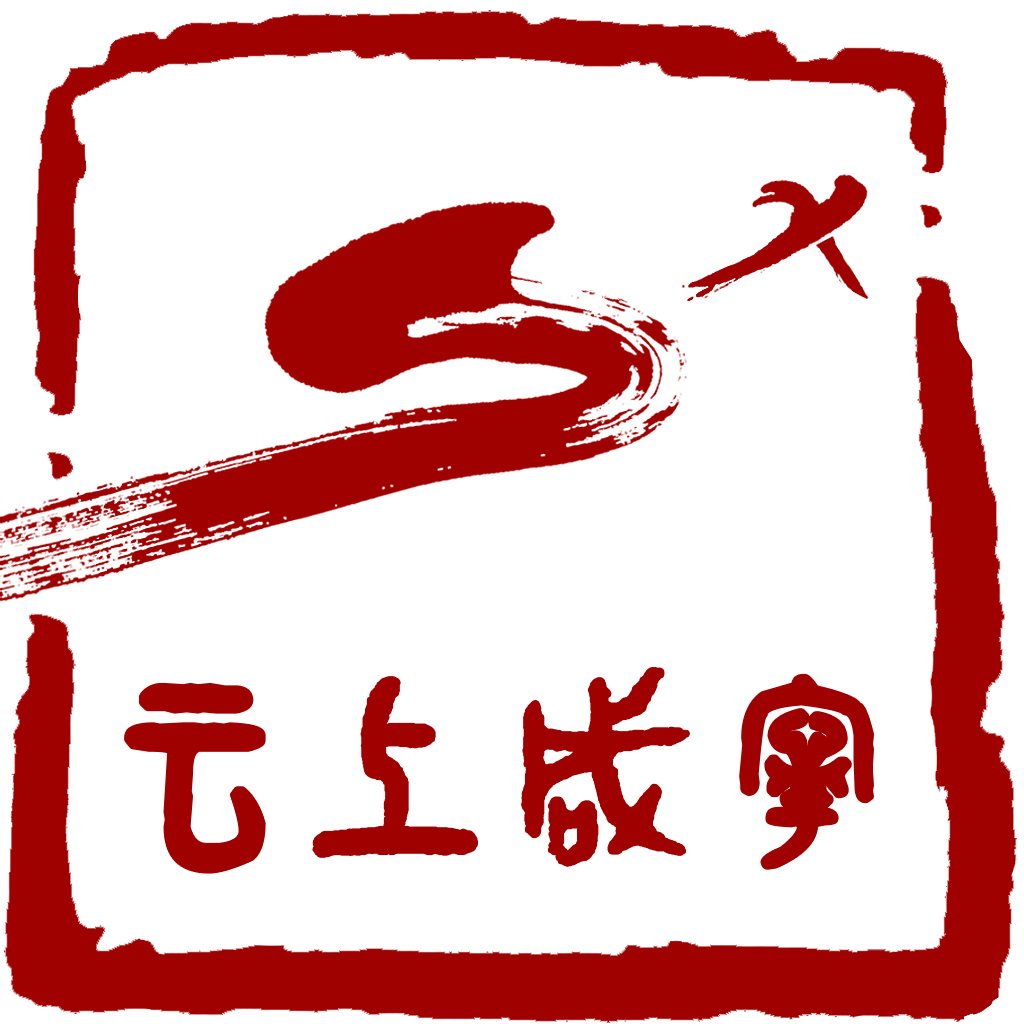云上咸宁报道(特约记者 胡剑芳)很幸运,我有三个父亲。一个是生我养我的父亲,一个是我上班后对我有恩认的干爸,一个是结婚后我的公公。

(网络配图)
三个父亲对我很好,各有特点。亲生父亲老实厚道,干爸为人爽直干练,公公处事温和。无论亲生与否,有付出有爱就会有满满的收获。让我拾些生活小事分享给大家,共享一分爱与被爱的快乐。
先说说我的父亲,今年76岁了,犹喜跟我一起唠嗑。听母亲讲,因为有两个哥哥垫底,父亲特别想要一女儿。我自打一生出来很受大家欢迎,特别是父亲,手托着我到处炫耀,“我有女儿了。”
父亲对我疼爱有加,凡事都让哥哥弟弟弟让着我,即便是母亲也不许骂我和打我。原因很简单,“我是女生”。我做错了事,父亲都可以带过,可哥弟们做错事,就得罚跪和罚站。比如小时候,父母总在外干农活,八九岁的我们就得在家里烧饭。经常摔破铁锅盖。凡是哥弟们不小心摔的,我都揽过来,都说是我摔的,因为有父亲护着,不用遭打。
可有一次,父亲把我打得很惨。那是上小学三年级那会儿,我学会了爬竹竿。爬上去后移身在2米高的树的侧枝上挂着玩耍,这让学校老师十分担心,怎么叫也不下来。后来,老师火速叫来在农田干活的父亲。父亲知我好吃糖。抓着一把糖吸引了我,我顺从地从侧枝到竹竿下一滑而下。这时,从未打过我的父亲用竹枝劈头盖脸一顿抽,边打边问,还爬不爬树到危险地去,直到我说不敢了才放手。为这,我一个星期没理父亲,尽管父亲一直跟我道歉。直到后来,我才懂得,这是最严厉的爱了。
读书那几年,因为家里穷,可父母却要我们四个一起上学,一个也不许落下。八九十年代,读书又贵,沉重的负担实在是把父母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上咸宁高中那会,一周穷得只剩下五元钱,每天只能买一元钱馒头和着开水填饱肚子。有一次,父亲来学校送来50元生活费,脚上还裹着泥巴。一个劲地说钱送晚了,是不是饿着了,我的喉咙哽哽地,泪水又一次汹涌而出。
出嫁那会,正安慰哭泣母亲的我突然看见在门角一旁偷着抹泪的父亲,这一幕触动我心灵深处的神经,我过去给父亲一个拥抱,说:“爸,开心点,我会常回来哈。”这时父亲才挤出笑容牵我的手送我上车。
寒来暑往,一幌多少年过去了,父亲老了。近几年来,父亲特多病,老慢支,哮喘,肺气肿,一年总要住上几次院。这时父亲总是喃喃道,死了算了,别这磨人。我们总是笑着安慰,“家有老是块宝呢”。 父亲眼睛看不清东西。我们兄弟四个带父亲做两次眼睛复明手术,父亲看东西总算清楚一些。一直以来,我们从来没有嫌弃地鞍前马后的照顾,这让父亲很安心。父亲老说,这辈子感谢母亲,给他生了几个孝道的孩子。

(网络配图)
对于我的干爸,那是我上班时认的恩人。上班那会,政府一时腾不出房子,暂住经管站长肖家(也就是我干爸家)几天,跟这家子结下深厚的情缘。
干妈是个朴实的女人,生了两个儿子没姑娘,对我自然是疼爱三分,像是自己闺女,家里只要有点好吃的总是想着叫我吃,或者跟我留着。只在有空,我总是喜往干爸家跑,抢着做家务干活,工作上也是吃苦很出色,年年都是系统内先进个人。
后来,干妈患癌卧床,每天我都会抽空去陪干妈说说话,帮她擦洗一下身子,洗脚等,希望能分散她的注意力,减轻些许疼痛。也许是为感恩吧,或许是什么别的原因,因为我真的有很多不舍。后来干妈还是走了,干爸一夜白发。这多年,只要干爸在家,我一年四季都会去拜望,无论有多忙,就象对生父那般。许多人说,真有良心,如此够了。我笑道,干爸一家视我如家人,我就得一辈子孝顺,多一个亲戚走动嘛。
后为还债(干妈病借),干爸到南方打工几年。前年再次知消息时,他出了一场车祸,断了几根肋骨。我急忙赶到医院,送来一些水果和牛奶,自己跟他儿子一起找肇事司机跑保险等。住医院那段时间,我经常探望,病友说干爸有这么个好姑娘真是有福。干爸笑而不语。

(网络配图)
我的公公是一个有文化的厚道老人,对三个媳妇都如同闺女,遇到困难总是全力帮忙。
记得我的儿子一岁时,老是吵夜。一个寒冬的晚上,我自己累得不行,任凭孩子怎样哭闹,我还是睡着了。半夜醒时,只见公公座在客厅沙发上,手中抱着孩子,还裹着小棉被,嘴巴还不停地哼着曲儿歌。一霎那,我感动极了,说道,爸,您去睡吧,我来带。没事,你明天还得上班,我带着,小家伙一放到摇窝里就醒了,只能在手上睡呢。
这一幕一直刻在脑海里,后来,无论有什么样的矛盾,想想这一幕,我气就消了。近两年来,77岁的公公身体大不如前。
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9时,我刚加班回家,老公电话我说,公公病了,让我去看看。我敲开公公家的门,见他蜷缩在沙发上,家里一股异味。婆婆说有几天不吃饭了,都尿失禁,还一直哼。我摸摸公公额头,有些烫,叫了几声都不回应。感到事态严重,我立即叫来二嫂一起送往市中心医院。
“肾结石积水,胃炎等,血液重度感染,必须马上消炎”,推着个床,楼上楼下抽血化验,做CT等系列检查后,医生要求马上住院打针消炎补能量。
“婆婆和嫂嫂说,曾打针晕过,不能打针, 48年来没打过针呢。”这可难到了医生,若不抗感染治疗,老人就救不了。否则只有转武汉医院。这大半夜的转院也不行呀。情急之下,我说,先给老人打个皮试看下。若能打再想办法打,医生接受这一建议。皮试显阴性可以打消炎针,但必须家属在告知书上签字。考虑到公公三个儿子大哥在深圳,二哥在武汉,三子老公又在妇幼上深夜班,冒着一家人埋怨,我拉着二嫂一起签了字。
经过一夜折腾公公沉沉睡去。我叫来护士打针,针打进去了,我一家人心又提到嗓子眼,十分钟过去了,半小时过去了,一小时过去了,没见公公有什么异样,心终于安了,就这样,一家人睁着眼睛紧张地一宿通宵到天亮,几瓶药水下去,公公真的好了起来。
“谁让我打针的?”得知是我时,公公怪我道,我几十年没打针,您想害死我呀。我笑道,想害死您也不会弄到医院来抢救呀。虽然一脸嗔怒,想想救回一命,也有些感激。
如今,公公出院在家,身体恢复好多。我常带儿子老公到公公那走动一下,一看老人身体情况,二让老人知道还有人关心着,很是满足。
这就是我三位父亲,我在其间,总在不同时间里,不同空间里,不同血缘中,被爱包裹着,享受满满的亲情与快乐。亲,你说,我是不是很幸福呢!
(编辑 陈玲)